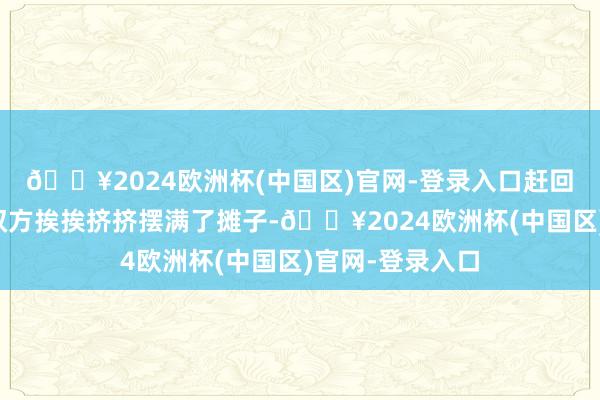
周末回乡下省墓,返程时走的是淮河大坝这条路。瞬息,前哨出现一派密密匝匝的东谈主群。老公跟一位肩扛树苗的老夫探问。“今儿个坝上逢集,你这车过不去了,掉头吧!”我俩一系数,干脆把车停在坝边,赶回淆乱去!
坝子双方挨挨挤挤摆满了摊子,卖种子的、修锅盖的、磨麻油的、握面东谈主的、耍把式的、打居品的……大木盆里养着鲢鱼和老鳖,青色的河虾蹦来蹦去,不必问,详情是刚从淮河里打上来的,带着一股簇新的滋味;芦苇编的席子、柳条编的篮子、高粱秆编的筐子、麦秸秆编的针线箩散漫着朴实的气味;逛累了的东谈主坐在条凳上吃面饼喝心肺汤,那汤熬得奶白奶白的,香气飘出老远;炒豆子的老夫笑眯眯地用纯粹的大手抓起一把黄澄澄、弥散的豆子撒下锅,加糖,那伙小毛头在大铁锅里连蹦带跳、嬉戏打闹,“砰”的一声笑破了肚皮……
悄然无声中太阳从正头顶极少极少西斜下去🔥2024欧洲杯(中国区)官网-登录入口,光芒从防御的白光酿成柔软的橘红色,河面上镀了一层金,大坝的影子越来越长,风中有了凉意,牛羊“咩哞”叫着,恋家之情散漫在空气中,不知谁吆喝了一声:“收摊,回家喽!”东谈主们纷纷拾掇东西、平安散去。我和老公牵入部属手欢欣地走在坝上,筹议着何日再来赶这充满乡村炮味的“坝上皆集”。
